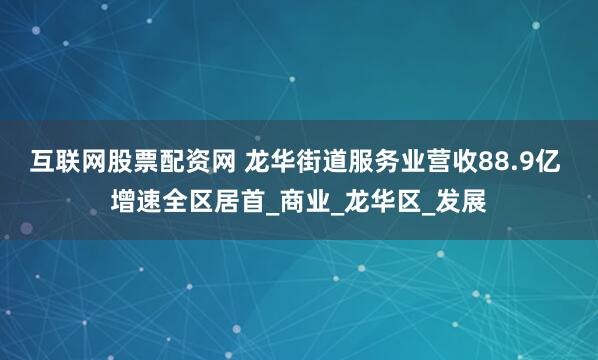所谓十九年七闰法,是一种将太阳历与太阴历巧妙结合的阴阳合历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在19个阴历年中插入7个闰月,这样计算出的总天数与19个回归年基本吻合,从而实现了对太阳运行周期和月亮运行周期的协调统一。以现代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水平来看,这种历法调整或许显得简单,但在人类文明早期互联网股票配资网,这堪称是一项划时代的历法创新。
要理解这一历法的精妙之处,我们需要先明确阴历和阳历的本质区别。阴历完全依据月相变化制定,以月亮完成12次圆缺周期为一年,这样的一年仅有354或355天;而阳历则基于太阳运行规律,以太阳连续两次经过春分点的时间间隔为一年(即365.2422天),不考虑月相变化,平年365天,闰年366天,每四年设置一个闰年。当今国际通用的公历就是阳历,而中国传统的农历则属于阴阳合历。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西方学界认为巴比伦人和古希腊人通过天文观测和数学计算先后独立发现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律,那么中国古代又是如何掌握这一历法奥秘的呢?中国史籍记载的发现过程与西方有着显著差异。
展开剩余81%首先,中国古代是如何测定回归年长度的?观测月相变化制定阴历相对容易,但阴历每年比实际季节变化要少11天左右,十年累积误差就达111天,完全无法指导农业生产。因此,中国这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必须发展出精确的阳历体系。那么,古人是如何测量回归年长度的呢?
最初采用的方法看似简单却非常有效——立表测影法。
通过测量正午时分日影的长度变化,古人首先确定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四个关键节气。考古发现表明,距今6500年前的河南西水坡遗址龙虎大墓中已有分至四神的图案,证明当时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年365天的基本认知。史书记载帝尧时期测算出一年为365.25天(与西汉四分历的年长一致),其真实性虽难以考证,但长期积累的0.25天误差确实会对农业生产造成显著影响,这必然会引起古人的重视。也有可能后世天文学家通过观测推算出这一精确数值,而后将其归功于上古圣王。
与中国不同,据说古埃及人通过观察尼罗河泛滥前天狼星与太阳同时升起的天象,测算出一个回归年约为365.25天。理解一年有365天尚属合理,但要精确观测出0.25天的余数实在令人费解。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巴比伦还是古希腊的记载都存有诸多疑点。特别是巴比伦人竟然计算出比中国更精确的回归年长度,其计算方法至今成谜,而中国则是通过实际观测得出的数据。
其次,中国是如何发现十九年七闰规律的?理论上,只要大致掌握回归年长度就足以指导农事活动,但月亮运行对古人而言意义重大,且月相变化便于计时,因此产生了调和阴阳历的需求。
《史记》记载,早在神农时代,古人就已意识到日月运行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直到黄帝时期才真正掌握其中规律。《史记·孝武本纪》中记载,西汉时期的公孙卿发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即19个回归年为一个完整的朔旦冬至周期,古人称之为一章。
尤为关键的是,黄帝是通过迎日推策的方法,经过20个周期(共计380年)的持续观测,才最终确定了阴阳合历的完整周期。在实际观测中,由于需要理想的天气条件(晴天才能进行日影测量),要确证十九年七闰规律可能需要更长的观测时间。虽然黄帝不可能真的活了380岁,但这一记载反映了古人长期系统观测日月运行的历史事实。先秦时期确实存在许多天文世家,积累了大量的观测数据。现代考古发现也证实,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
由此可见,中国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天文观测才发现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律。历法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其发展必然遵循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需要长期的数据积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轨迹完全符合这一科学逻辑。
当我们厘清中国发现十九年七闰的历史过程后,再审视西方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其中存在诸多令人费解的神奇之处。
首先,据称巴比伦人通过观测发现月相周期与季节变化存在差异,然后计算出回归年长度(具体观测和计算方法不详),继而发现了十九年七闰规律。但阴历与阳历每年相差约11天,而季节变化往往并不明显——比如立春后11天依然寒冷,立冬后11天仍然温暖,巴比伦人是如何准确判断季节变化与月相周期的差异的?在不清楚回归年精确长度的情况下,又是如何确定十九年七闰的?
其次,约2400年前,希腊天文学家默冬通过观测日月运行周期,发现19个回归年与235个朔望月几乎等长,从而提出19年7闰的方法,后世称为默冬章。即便假设古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获知了回归年长度(这一点本身就存疑),考虑到默冬有限的生命年限和观测受天气条件限制(某些天象一年只出现一次),他能够完整观测多少个19年的周期?如果仅观测到一两个周期,又如何能确证十九年七闰的普遍性?
发布于:天津市中金澳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